永遠的記者,一生的使命張作錦《姑念該生》編後│沈珮君
一個17歲的小小兵,吃不飽,瘦到連槍都舉不起來;他被打到受不了,作了逃兵。小逃兵走投無路,餓得在街頭撿東西吃,成了遊民。好不容易做了小工,有吃有住了,但不堪被當傭人,最後仍回到軍隊作小兵,卻又天真爛漫寫信「自首」,跟原本的連長道歉當時「不辭而別」,並老老實實報告他現在某單位,淳厚的傻小子因此變成通緝犯。他只好改名,卻又在24歲因病被列「老弱殘兵」,強制退伍。他無家可回,但沒有自暴自棄,找到工作,並準備考大學;第一次落榜,第二次數學零分,但其他科目甚好,以28歲高齡考上第一志願,政大新聞系。但災難還沒結束,他大二時被指高中學歷有問題,教育部勒令退學,最後留校察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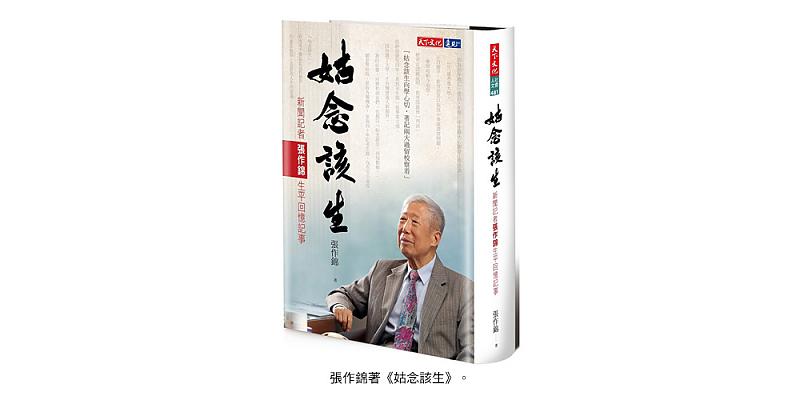
這個小小兵,若用今天的話來說,就是「魯蛇」。誰也想不到當年的魯蛇最後做了《聯合報》總編輯、社長,健筆如椽,僅評論文字逾百萬字,出了13本書,在84歲時得了總統文化獎,85歲獲頒二等景星勳章,88歲出版20萬字的生平回憶記事《姑念該生》。
張作錦先生,我們在報社稱他「作老」,直到現在他走路都像個小小兵,快速敏捷。他身分證上的生日是「4月4日」,兒童節。就跟他的高中文憑一樣,他的生日也是「時代產物」,他不知道自己生在哪一天,他說,選兒童節,只是因為好記。我覺得不僅如此,那是一個在軍中屢遭責打的孩子想爹娘。他對父母的孺慕之情,終其一生「相思無從寄」。
這個孩子一次兒童節都沒有過過。作老也不願意過生日。
作老六歲就成了孤兒,父母直接、間接死在共產黨手上,他一生的心情就是「孤臣孽子」。那時沒有「亡國感」這個詞,而「亡國感」卻是每天壓在肩上、心上的日常。
誰與斯人慷慨同
「亡國感」,現在被網友戲稱「芒果乾」,當年是「退此一步,即無死所」,是死生大事。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,「毋忘在莒」、「臥薪嘗膽」,從總統到小學生都拳拳在心,就是這種強烈的亡國感,上下一心,自強不息,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。易經「乾乾夕惕若厲」是那個時代的精神,也是作老一生奮勉憂懼的寫照。我們曾經輝煌,李登輝承繼蔣經國留給他的總統職位時,正是「台灣錢淹腳目」,而現在三度政黨輪替,不論是政治民主或經濟民生,我們愈來愈好了嗎?仍在「自強不息」嗎?
這幾年,作老有些力不從心了,但仍「風雨如晦,雞鳴不已」,希望「江山勿留後人愁」。2015年,他終於決定結束長達27年的專欄「感時篇」,發表〈告別讀者〉時,一個讀者打電話給《聯合報》編政組,哭著說,「我們了解什麼是灰心,但是,請張先生不要停筆」。作老這個孤臣孽子最後一本時論集是《誰說民主不亡國》,亡國感直接入題了,「心所謂危」已到何等深切。
作老瘦弱,筆下卻有千鈞之力,厚重,哀傷,讀他的書總像被人一下一下搥著胸膛。我跟作老相差近30歲,初讀他的舊作時,還不認識他,忍不住驚嘆,這是什麼先知先覺的高人。台灣現在的問題,他在二、三十年前早就直接指出了,很多讀者因此推崇他,他卻毫無「吾道不孤」之感,他說「作為作者,哀矜勿喜」,他憂心忡忡,「台灣幾十年的政治、社會問題,絲毫未改,這是衰亡之兆,而覆巢之下,孰能倖存?」
作老是快筆,但這本回憶錄卻歷時4年,是他一生最艱巨、漫長的寫作工程,內容和他實際人生相比,簡約過甚,一因他謙抑,他認為「斯人也,小子也」,怎能「托大」寫回憶錄?即使書成,他堅持不肯在書名用「回憶錄」三字。二因他長年做總編輯的性格。在《聯合報》,丟掉的稿子比刊出的多得多,他對自己記憶體的資料,「選稿」、「核稿」甚嚴,一度認為撰寫本書根本是「棗災梨禍」,寫寫停停,若非各方好友勸勉甚殷,幾乎不能終篇。三因他不願道人之短,就算有所謂「內幕」,點到即止。還有,那個家破人亡的時代,多少創傷,年少時即已封存,老時尤不能觸碰。
鄉關何處
「人情同於懷土兮,豈窮達而異心?」他的「土」是整個大中國。翻攪這幾十年的回憶,其實沉重。做為他的主編,我看著他受的折磨,經常不忍。
家在哪裡?
認識作老的人,都知他的性格堅毅,但我看過他流淚。
他在寫〈許倬雲的三次眼淚〉前,我先聽他說了。其中一次,時代背景是抗日戰爭,許倬雲家住長江邊,那天,許多小兵上岸,川流不息,許媽媽把小許倬雲放在門前石獅上,自己忙著替他們燒開水,媽媽告訴許倬雲,「那些孩子從這裡走過之後,可能再也回不來了」。中日那八年極慘烈、極不對稱的戰爭,中國的「血肉長城」就是一個個這樣的年輕人用父母給的身體堆起來的,中國因此沒有亡。長大之後成為中研院院士的許倬雲,在跟作老說這段往事時痛哭流涕,作老在跟我說時也滿臉淚痕。
沈君山和作老相交半世紀,兩人往返書信如赤子。沈君山第二次中風後,曾在聯副發表〈二進宮〉,公開他已交給律師及親人的遺囑,聲言絕不要無謂的急救,但在第三次中風倒下後,臥病11年,遺囑竟不能執行。這樣一個風流倜儻的瀟灑公子,這樣一個在二次中風之後仍「尚思為國戍輪台」的血性男兒,半生奔走兩岸,三見江澤民,想為中國「一而不統」鋪路,不料最後竟不能為自己生死置一辭。「悵望千秋一灑淚」,作老每到醫院或赴新竹寓所探望他,往往掩面失聲。
永遠的記者,一生的使命
作老喜與文人相交,所謂文人就是知識分子,以前知識分子不是指高學歷,還講究氣節、操守、人品。作老對他敬仰的知識分子,幾乎是執弟子禮,經常親訪或邀稿,替《聯合報》在學界建構了龐大的人脈網,並創設「專欄組」,將《聯合報》一舉推升到成為知識分子的公共論壇,一改當年以社會新聞為主要報導題材的媒體現象。
作老即使當過總編輯、社長,在拜訪大陸紅學專家周汝昌時,親自採訪、撰稿,從照片上可以看到,他的膝上擺著筆記本,身體前傾,神情之專注興奮儼若中小學生。那時他已73歲。
作老一生只有一個工作:新聞記者。他認為總編輯只是暫時的行政職,終生職是記者。記者不是職業,是職志;不是一時的工作,而是一生的使命。總編輯卸下行政職,就應回到記者本業,或輔佐現任總編輯,這些珍貴的資深人才應該一直留在戰鬥崗位。他始終不認為這想法是「不食人間煙火」,30年前的建言未被採納,仍把它寫入「生平記事」,這已不是「若有憾焉」。
作老72歲退休,73歲去北大「遊學」。他常說,他一生最嚮往的生活是「青燈黃卷」。他自小失學,對知識的渴望、崇慕,貫穿一生。他視力很差,讀書費力,隨著年紀愈長,閱讀愈困難,他發明了一種「張氏大字本」,把剛買的新書拿去影印放大兩三倍後再讀,這種大字本,他有四、五十冊。他一直希望出版社能出大字書,這也成了他未了的心願。
作老「任謗」,有時,旁人替他氣得跳腳,他卻如局外人。他當年為報社做了許多改革,當時第三版幾乎都是以犯罪新聞為主的「社會新聞」,閱讀率很高,但是,作老認為應讓重要版面轉型為各種值得關注的「社會議題」。這在當時是嶄新的觀念,而那些當年被作為議題設定的深度報導,不像現在如狗吠火車,那些報導對當年民主、民權、民生、民智,都發生極大影響力。但這種改革不免影響了專跑警政新聞的記者見報率,有人至今仍恨恨不休,而作老早已「菩提本無樹,明鏡亦非台」了。
曾任《聯合報》21年總主筆的黃年先生,從實習記者就和作老共事,他形容作老是一個「上上下下,人前人後,為人為文,表裡如一」的人,這幾字甚平淡,做來甚不易,而作老自然而然,不費吹灰之力,因為他就是這樣的人。他是《聯合報》唯一一個退休後還有自己辦公室的人,可見報社對他的禮遇,他在辦公室寫作不輟,成為第一個拿到總統文化獎的媒體人。這位白髮蒼蒼的老聯合報人,至今仍搭公車上下班,進出報社和一般同仁一樣佩戴員工證。如果早上在報社一樓聽到超商小七的小姐高聲喊著「大哥,你的中熱拿好了」,那位快速躬身上前去拿咖啡的「大哥」,常常就是作老。
心血肉相連的那種疼
作老喜讀田園詩,他曾以陶淵明為例,無論是〈五柳先生傳〉、〈桃花源記〉、〈歸園田居〉,文中滿滿的「人」,而且是「他人」,不是「自己」這個人。作老的回憶記事也很少自己,以事為主,從事看到那個時代;寫到人,也多是友人,而提到友人也多和那個時代的事有關。最後,在我再三催問家庭細節下,他寫了〈三個媽媽誰是娘〉,那是他一生的大哉問,家園和國家「心、血、肉相連的那種疼」,躍然紙上。
他連徬徨都不是一家一人而已。他的心裡沒有自己這個「人」,而恰恰是因為這樣,成就了他這樣一個人。一個文化人,一個知識分子。
(作者係資深媒體人)
附加資訊
- 作者: 沈珮君
- pages: 46
- 標題: 永遠的記者,一生的使命張作錦《姑念該生》編後




